“新藏线”难忘的往事——马新民
1970年,知青招工,我被招到喀什中心运输站。1972年,单位派我到“新藏线”的三十里营房站担任炊事员。
三十里营房,海拔3780米,那里高山环绕,气候恶劣,与喀什比起来,条件相差甚远。但那时的年轻人,大多不会跟组织讲条件,更不敢与组织抗衡,而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从那时起,我便步入了“新藏线”,开始了在人烟稀少的“新藏线”上燃烧青春的岁月,这岁月一烧就烧了15年。随着工作地点的不断变换,阿里、库地、麻扎、三十里营房、狮泉河、日松……这些“新藏线”上的地名都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当年的辛苦与幸福,随岁月流逝变成了的记忆。老了老了,喜欢忆旧,2022年夏天,忆旧的心态驱使我与妻子和大舅哥一起重走青春路,再上“新藏线”。不料行程刚刚开始,就被新冠疫情阻断,我好失望,写下了《故地重游梦未圆,疫情无情人有情》。
2023年夏天,我们三人又踏上了圆梦之旅,所幸一切顺利,我陪他们走了他们要走的地方,他们也陪我走了我要走的地方,而那次,我的重中之重就是 “新藏线”。第二次行程结束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酝酿了好久,又写了新作《再踏圆梦之旅》。
前后两年,两次出行,写了两篇文章,我的心灵似乎宁静了许多。可是,今年夏天,宁静的心海又被一张张照片激荡得浪花飞溅,我不由得再次拿起笔来要一书青春的浪漫与活力。
什么照片呢?是大舅哥和小舅子拍摄的照片,照片就来自于“新藏线”。我佩服大舅哥,他随我们夫妻走了一趟“新藏线”后,竟然意犹未尽,带着弟弟又走了一趟。而且一路走一路拍,拍了就发给我们。看着那熟悉的山山水水,我的思绪自然而然又飞回了遥远的过去,飞回了现在想起来还那么生动与激情澎湃的往事之中。
一、麻扎兵站疯狂乒乓
在“新藏线”工作,工作人员都是5月上山,一直要干到11月底撤站时才能下山,每年都一样。
1972年,我从三十里营房下山,坐的是站长给联系的军车。因为坐了军车,所以发生了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地方,名叫麻扎,从三十里营房下山要路过此地,它距离叶城约240公里。虽说麻扎也在“新藏线”上,但它并不是我们交通系统设立站点的地方,按说我不应该和麻扎有什么交集。可是麻扎有兵站,我坐军车,机缘巧遇我就进了麻扎。没想到,那因为乒乓球让我对“麻扎”这个地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上午十点左右从三十里营房出发,中午1点多到了麻扎兵站。兵站设在距离公路2百米左右的山沟洼地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就是从这个山沟走的。吃完午饭后,我坐车的那个驾驶员说要打打乒乓球,他说他是个乒乓球爱好者,是打起球来能忘掉一切的那种人。
这点与我不谋而合,我也喜欢打乒乓球,但没疯狂到他那种地步。我属于可以打的时候就打打,没地方打也不谋着打的那种人。所以听他那么爱打乒乓球,我并没说自己会打,主要是怕人家打得太好,跟自己打没意思。打乒乓球与下棋一样,要旗鼓相当才能玩出兴趣来,这是一般人都懂的道理。
我随他进了兵站活动室,室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乒乓球台。说非常漂亮,可真是漂亮,起码是我见过的个最漂亮的球台。
一进去,他就和兵站的人打起来,一连打了几个人,谁都不是他对手,有人甚至打的是和平球。打了一会儿,他打得没劲,说不想打了。我说:“我和你打几个球好吗?”他非常高兴,递我一个球拍,我一看是红双喜的拍子,用的球是光荣牌的,我也异常高兴,我还从来没用过那么的拍子。
我们家人似乎和乒乓球有缘。兄妹四人中,只有老三不打乒乓球,我哥、我妹和我都打,只不过我的水平和他们比起来差了一截子。
我哥招工招到了乌鲁木齐铁路局,当了一名铁路工人。他在乌鲁木齐铁路局乒乓球比赛中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开始一些年,别人打不过他,后来看有些年轻人比他厉害了,他干脆把球拍换成了长胶。他换长胶是长胶刚刚推广的时候,拍子一变,年轻人也打不过他了。他不仅乒乓球打得风生水起,羽毛球也是他的拿手好戏。这两项都是他代表乌鲁木齐参加全国铁路系统比赛的项目。后来铁路局有了网球场,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网球上,保留了羽毛球而舍弃了乒乓球。
我哥从年轻20几岁到60多岁,一直驰骋在球场上,直到有了外孙女后,上有80多岁老母需要照顾,下有新出生外孙女需要喂养,他才不得不放弃球场,过起了没有打球陪伴的日子。
我妹1971至1973年,连续三年是喀什地区少年女子单打。那三年,没比赛的时候每天下午课后去业余体校训练,有教练指导。比赛前还要住在体委大院封闭训练半个多月。她那时候的乒乓生涯属于半专业化了,这种半专业化的训练,为她奠定了坚实的乒乓球基础。原本可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1973年,开始抓教育了,父母不让她再打球,要她专心学习文化课。体委领导惜才,两次来我家做工作,都没做通,我妹妹的半专业乒乓球生涯也就戛然而止了。
不过后来我妹也打球,就是到现在,生活在北京,还在球场上一决高下,打得不亦乐乎,时不时还从微信上给我们发打球的视频、照片和文章。她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在北京得奖了——我的人生路,我的乒乓情》。
写麻扎兵站打球,又绕到了我家兄妹身上,是因为我想写我特别有记忆的一次打球经历,那就是我们“马家军”对阵喀什六运司。
虽然我比我哥我妹差,但在一般场子上打打,还是有点实力的,每次看到别人打球,心里就痒痒。加上有哥和妹这个实力,所以在我哥回家探家的时候,我还喜欢跟一些单位约着打比赛。
有一年年底,我去喀什六运司办事,一进六运司办公室的过道,就听到了“乒乒乓乓”的声音。这时,我没想着办事,反倒循着乒乓声走过去了。我来到一间比较大的房子,里面放着一张乒乓球桌。看来这张球桌是两用,既当会议桌又当球台。当时有几个人在打球,其中一个打得更好的叫曹伟光,是六运司子弟学校的老师,我认识他。其它人虽见过但不熟。
看了一会儿,其中两人有事先走了,我说:“曹老师,我能和你打一下吗?”曹老师高兴的说可以可以。我们练了几个球后,曹老师想打比赛,这正合我意。大多数野路子出身乒乓球打得有点水平的人都比较爱打比赛,因为基本功练不起来,而打比赛就比较有趣了。
我们打了三局,都是曹赢,那时候是21分制,我每局输他4、5个球。曹伟光是六运司的乒乓球,我给他聊起我哥我妹都是喀什地区喀什市的青少年乒乓球,他俩都到色满宾馆给外国人打过表演。
曹老师一听,马上说你把你哥你妹叫来和我们六运司打个团体赛吧!我高兴得不得了,当即答应并约好了时间。那天比赛,我马家兄妹5比4战胜六运司。哥一人赢了3人,我和我妹各赢一人。
若说“马家军”对阵六运司让我记忆深刻,但比起麻扎兵站打球,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麻扎兵站打球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为什么?一是乒乓球案子在我眼中很,二是拍子是我从来没用过的更好的拍子,三是那天打球我达到了疯狂。
我和驾驶员开练了几个球后,他感觉和我能打到一块,就说咱们现在正式比赛。这就是上面我说到的,觉得自己打得好的人都愿意打比赛。我们打了一场,21分制,5局3胜,我赢了3局。每局比分都比较接近,也就两三分之差。打完这一场,我俩都满头大汗。
刚坐下来休息,车队带队的人来了,说今天要住库地,大家都要走了,催我们快走。他们一个车队,同行有好几辆车。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驾驶员给带队的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对手,要和我好好打个痛快。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领导竟然批准了!
当时我想,这可是部队啊,军令如山倒,这位驾驶员怎么敢提出这样的请求?而他的领导为什么又能轻易批准他的请求?总之,在我心里不可能的事都成了可能,那我俩就放开打吧!
我们从中午打到下午吃饭,饭后又打到晚上,一直打到兵站熄灯没有条件再打的时候才罢手。那时兵站自己发电,停止发电的时间是11点。也就是说,那天我们起码打了7、8个小时。
就两个人,打了7、8个小时,那是多么大的瘾啊!那天我们完全成了地地道道的乒乓球瘾君子。当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瘾,是因为我俩水平接近,当将遇良才棋逢对手时,自然就忘了时间,忘了劳累,忘了一切。
那天我俩打一场5局3胜,就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打5局3胜。输赢不是一边倒,而是平分秋色,你赢完了我赢,我赢完了你赢,而且每局比分都咬得很紧。所以那天在名不见地图的麻扎小兵站上演的乒乓球大战够意思。
我们各自的那种斗志、那种气势、那种想赢的心态,不亚于现在的世乒赛,遗憾的就是没有观众,没有喝彩,没有掌声。当然,我们的水平跟世界高手的水平那是天地之别,但除了竞技水平之外的一切是不是都差不多呢?
天坐车,一路我们没说几句话,通过打乒乓球,我俩的话就多得说也说不完了。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把新藏线上所有的兵站都打遍了,从没遇到过对手,我是个”。第二天我们赶到了叶城,他把我专程送到了运输站。我们彼此问了对方的名字和籍贯,时间一长我现在只记得他是从四川入伍的,名字早就忘了。
虽然忘了他的名字,但忘不了和他打球的故事,更忘不了一个原本与我工作无关的“新藏线”上的地名——麻扎!
麻扎,那是我疯狂乒乓的见证地,是我打乒乓球打得最汗暢淋离的一次,要说我俩那天是乒乓傻子,一点也不为过哪!
二、多玛日松区买羊受天大委屈
1973年,我上“新藏线”,工作地点是多玛站。这一年,我被任命为多玛运输站管理员,身份是“以工代干”,这是我今后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起点。在多玛站工作最让我难忘的是买羊那天所受的罪,尤其是所受的委屈。
多玛隶属于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640米,属于高原山地气候。买羊的事发生在阴历10月15或l6。
从阳历上说,这个时间是11月中旬,多玛的气温已降至零下一二十度,随着天寒地冻,我所在的多玛站也要撤站了。但当时我们还有50只指标羊没弄回来,羊指标是批给日松区的,想要羊就得派车去日松区。我们站长和喀什六运司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过过江的老资格驾驶员关系特别好,站长派我坐他的车把羊拉回来。
多玛到日松区大概有一百五六十公里,我那时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途中会发生什么,所以根本没做任何准备,只带了买羊的钱和皮大衣就出发了。
我们先是很顺利的到了日松区,日松区刘区长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安排了一顿说中午不中午说下午不下午的中晚歺,还带我参观了库房,库房里堆得满满当当,其中一个大箱子里装得满满的是袁大头,随便可以拿。我抓了一把,一数是6枚。
随后刘区长给我们找的向导来了,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藏娃。我们往日松区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车到了日松区还要往放羊的牧人家里走,没走几公里就下了公路,汽车开始在戈壁滩上行进。
大概走了一二十公里后,看着前面依旧戈壁平平,也没什么障碍物,可不知怎么车就突然陷入了一条暗河中。师傅一下急了,三拱两不拱,车子的6个轮子全部陷了进去,保险杠大箱底板也都快挨着地了。
危难时见真容,这位抗美援朝过过鸭绿江的师傅顿时变了脸,一边说“完了完了”一边埋怨我,说“都是为了给你拉羊,现在远离公路叫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报救急都没法报。”小藏娃给我比划他去找人来,比划完就走了。
抗美援朝的驾驶员这时候更绝,他看天快黑了,就把水箱的水放了,然后把他的皮大衣往驾驶室的座垫上一铺,把我的皮大衣一盖睡起了大觉,而把我丢在了车外。
昆仑高原11月的天,天是那样的冷,而我却只穿了一件绒衣一条绒裤,还是在河边,可想而知我有多冷了。好在距离车辆抛锚5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有2一3间房子大小突出地面的风化岩石,而且岩石都是片装,我拿半截钢板一橇就是一块,体积不大也不小,我抱着也不是太费劲。另外车上还有两个特别好用的苏联千斤顶。
老天可能知道我难,晴空万里没有一絲云彩,月亮圆圆的特别亮。在月光下,我一趟趟的搬着石头,石头搬得差不多了,我用钢板在车子的前后能支千斤顶的地方挖一个窝放上石头,石头上支好千斤顶开始打千斤,一个千斤打起来了,赶紧换另一个千斤,千斤一松放在下面的石头就陷下去了。
这个千斤顶的活可把我坑苦了,支好了塌、塌了再支,反反复复支千斤,搬的石头根本不够用,所以我又反反复复去搬石头,50米距离的搬运石头我来来回回走了不下100趟。费了太多太多的气力,终于把车的所有轮子顶了起来。
这个活,若有人在一旁搭把手,会容易好多,可人有,也近在咫尺,只隔着一层车皮,却车内车外两重天。车内的人全身暖暖呼呼大睡,车外的人无助无奈到了极点。那天晚上只有月亮是我的陪伴,我劳作着,时不时看看月亮,那晚的月亮非常美,圆得出奇,也亮得出奇,多看几眼月亮自己的心情似乎能够得到一点点调整。
一夜时间,我才把6个车轮都顶了起来。天已大亮,车门依然没开,只是传出呼噜声。我心里那个气呀,可又没法说。接下来我又用石头把轮胎拱出来的坑都填好,又顺着车轱辘在暗河上铺了一条路。
那天从晚上干到第二天中午,一干就干了近20小时,可以说一分钟没停,不是不想停,是不能停啊,停下以后光那个寒冷我就没办法抵御。
中午时分,我拍了拍驾驶室的门叫师傅下来看看,没想到他摆着手说“没门没门”。刹那间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把车门拉开,他枕在车门上的头一下子掉了下来。他刚要发怒,但看了一下我灰头土脸的样子,他下了车,又看了一下我的劳动战果,激动坏了,说“可以!可以!你看着我把车开出去。”
车开上路面,我用他的缸子在陷轮胎的坑里取水加满了水箱,他问我向导往哪走了,我指了一下方向,他按我指的方向开车前行。不一会儿,就看见小藏娃向导带了8一9个人、十几匹马、绳子、铁铣来救车了。
当他们看到我们,都惊奇不已,语言我听不懂,但表情神态能知道,他们在说没想到我们自己能出来。同时也特别高兴,因为来救车的八九个人没有坐过汽车,所有的人都想感受一下坐汽车的滋味,但十几匹马还需有人赶回去。后来他们在一起做我看不懂的动作,向导对我比比划划,我才知道,他们在玩游戏,类似抓阄,是用这种方式确定谁把马赶回去。
再次上车之后,我便昏睡过去,到地方才醒来。牧羊主家给了我一条半干不湿的生羊腿,管它是生是熟,只管吃。我先是拿刀割一块放酥油茶里沾一沾吃,后来看刀子不快割一块肉要费好大劲,就干脆抱着羊腿啃起来。说着你可别不信,一条羊腿没用多长时间就被我吃光了。
紧接着老乡给我们做的揪面片也做好了,说是面片,其实就是面疙瘩和面糊糊各一半,不知是谁给他们送的生西瓜,他们带皮都放到了饭里,就这样的饭我也吃了好几碗。
羊买好后车在路过日士县时发电机又坏了,而我的裤子也在忙忙碌碌中被刮了一个大口子,是日土县一个姓李的姐姐给我缝上的。这件事对她来说可能小事一桩,对我来说,却值得感激一辈子,人在难处,这是雪中送炭啊!
反过来说,那位原本令我尊重的抗美援朝出生入死的师傅从此我很看不起他了,尽管事后他到处夸我,夸我多能多能,夸我多好多好,但夸得再多也无法抵消那天晚上他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伤害。
那天晚上的我啊,又冷又饿、又累又气,最关键的是又无奈,明明知道他欺负我,我还不能说,那种委屈、那种悲凉无助的心态比起饥饿寒冷和劳累,更让我无法忍受。所以,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这个有着抗美援朝金字招牌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无论他再怎么夸我,在我眼中他一分不值!
曰松买羊,车陷救车的近二十个小时让我刻骨铭心。什么叫饥寒交迫?什么叫累得要死?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忍气吞声?我都体会得淋离尽致。那天晚上让我感到温情的是那圆圆的月亮,为什么我把这件事的时间定格在阴历的10月15或16,就是那晚月亮给我的记忆。
三、库地兵站饮酒如喝水
50年前的八一建军节是我这一辈子喝酒最多的。
1974年,我“新藏线”的工作地点是库地。“八一”这天,库地兵站邀请站长和我去兵站共庆建军节。到了兵站,他们的桌子已经摆好了,是用两张办公桌拼起来的,地点也不是餐厅,而是指导员的办公室。
菜上齐了,兵站站长在我和站长的面前各放了一个缸子,这缸子是部队统一配发的,能装750克水。说起这样的缸子,现在年轻人不太熟悉,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那容量可真不小。
指导员叫年轻小兵给我和站长倒酒,小兵很听话,也很认真,给我们两人的缸子实打实的倒满了酒,满得都端不起来,只能先爬着就着缸子喝一口才能端。老话说:茶半杯,酒满杯嘛,倒酒满到这种程度,显示着人家的热情与诚意。
酒是叶城4号地(部队的农场)生产的60度的苞谷酒。那个年代酒非常难买,所以能喝上酒是非常幸福的事。在一般的桌子上喝酒是劝酒,在部队的桌子上喝酒就不是劝,而是多少带那么点命令的味道,军人的习惯就连表达诚意也带着点命令的味道了。
酒倒好后,指导员对我的站长下达命令:两缸子酒是你们运输站的酒,你们必须喝完!
实话说,以前我喝酒的次数少得可怜,只有两次记忆。
一次是上中学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时,我和同学金日照、李风奇在老师的办公室搞了好多报纸,卖了,卖报纸的钱我们买酒喝。
记得当时买了一斤半酒。没有喝酒的杯子,怎么办呢?李风奇有办法,不知他怎么有一个100瓦的电灯泡,他竟然把灯泡金属底座部分取掉了,只剩下玻璃灯泡。
酒就倒在了灯泡里,我们三人端着灯泡喝酒,在没有任何下酒菜的情况下,一边说着话一边喝,一阵干喝就把酒喝完了。喝完后我没事,他俩却醉了,我拖一个拽一个,把他们送回了学校。
第二次是招工到喀什中心运输站工作后,有一次古尔邦节给维族职工拜年时喝过一次酒。
拜年一大拨人同去,就是现在所说的“团拜”。维吾尔族的家都铺着地毯,大家席地而坐,中间桌子上摆满了干果馓子油果子等。主人给大家一一敬酒,各家酒杯大小不同,有大的,有小的,即便是小的,一杯也有一两。
每家都是喝一杯走人。我们拜年帮就这样走了一家又一家,喝了一杯又一杯。走的家越多,去拜年的人数就越少,不少人都因喝醉酒回家了,可我一直到最后也没什么醉意,身体没醉态,大脑清楚,说话也沒有大舌头。
这两次喝酒之后,我再没沾过酒。但因为有这两次喝酒经历,我对酒的厉害根本没什么感觉。那天在库地,看着满缸子酒,我毫无怯意,不知道要在酒桌子上装一装,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别人的劝酒与敬酒。站长是久经酒场的老手,他是明白人。这时候他说他不能喝酒,沾点就会醉,所以他面前的缸子动都没动。而我则傻乎乎的把我面前的一缸子酒喝完了。
见我喝完没事,指导员他们让我把站长的酒也喝掉。我二话不说,马上爬到站长跟前的缸子上喝了一大口,然后一阵子吃着、划着、喝着,稀里糊涂又把站长的酒喝干净了。
两缸子酒下肚后,兵站几个小兵又领命从餐厅跑过来给我敬酒。那时候实际上我已经喝多了,越是喝多,越是无畏,敬酒我是来者不拒,无论是谁只要缸子端到我跟前,我就一饮而尽,当然,他们敬酒只是在缸子中倒一些酒,并不是满缸。
那,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喝了3斤酒,至于当兵的敬酒喝了多少就不清楚了,估计最少也有一斤。74年的“八一”是我一生一次性喝酒喝得最多的一次,从此以后我爱上了喝酒,也有了多喝酒的底气。多少年酒场上跟人拼酒似乎没怎么输过,但回到家就烂醉如泥,受了多少妻子、女儿和父母的叨叨已经不计其数了。
多少年来,喝酒好像成了我的生活常态,即便在家里,也时不时要独饮几杯,有酒佐餐,才觉得饭菜特别有味道。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60多岁,近几年不敢多喝了,有宴席的时候,也小酌几杯即可。
回想过去的岁月,真的没少喝酒,而开启我多喝酒的历程就是1974年的“八一”建军节,地点就是库地兵站。
现在想想挺傻的,库地海拔3150米,虽说不是太高,毕竟是“新藏线”上啊!在这种高度的海拔地区一顿喝那么多酒,喝出个三长两短不是不可能的,但那时我天不怕地不怕,就知道傻了吧唧的喝。
所幸我好像天生就耐酒,也幸运那天喝的酒是好酒,是粮食(包谷)酿造出来的纯粮食酒,更庆幸那个年代的人不会造假,所以喝了那么多竟然没事。
这事说出来挺丢人的,也没任何意义,但这确实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事,是让我永生难忘的事,所以无所谓人们咋样评说,我还是勇敢的把它写了出来。
……
上面写了三件事,事情虽然已过去了那么久,但在写它们的时候我还是热血沸腾,好像它们就发生在昨天。
在“新藏线”上的运输站工作,没有喧嚣的热闹,没有宽阔的马路,没有同学朋友们隔三差五的聚会聊天,看到的只是高山峡谷,看到最多的是牛马羊群,一起工作的同事只有几个人,到晚路过我们站里的人也不过十个八个。而我20出头到30多岁,青春最美好的岁月就留在了那里。
但我并不寂寞,在那里发生了许多城市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很难遇到的事情。比如:我种的大蒜中挖出了与成年人拳头大小的大蒜;我和别人一起抓到了十几匹近乎野马的马;我独自一人徒手捉住了一只黄羊;我时不时会收到放牧人送我的雪鸡、酸奶,有一次还收到了一条差不多有壮汉胳膊粗、近2米长的党参;在少鱼的大山中我一下午钓到了二三十条筷子长的魚;牧民们送的雪鸡吃不完,我还学会了制作腊肉的方法熏雪鸡……
如此等等,那里的生活虽单调但也别有情趣,别有乐趣,正因为那别样的生活,给我留下了太多别样的感受与别样的记忆,所以那感受,那记忆,一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栩栩如生。
难忘“新藏线”!难忘“新藏线”工作的点点滴滴!感谢大舅哥小舅子替我再走“新藏线”,激发出我的激情,让我“老夫聊发少年狂”,又写出了这篇回忆录!
2024年11月
推荐资讯
- 婚宴用酒怎么选择呢?2020-09-01
- 瓶装酒存放必须要知道的细节 !2020-09-01
- 散酒中存在哪些重要指数?2020-09-01
招商推荐

- 原浆进口OEM贴牌葡萄酒
- 类型:
- 热度:

- 我要加盟
- 白酒动态
- 啤酒动态
- 红酒动态
- 「酒文化」“哥俩好、五魁首、六六六”,这些行酒令你都了解吗?
- 破解酵母活性限制难题 千年米酒在湘获技术突破
- 加油站=大超市,服务,就是这样认真
- 酒业观察丨营收 20亿-50亿,区域白酒竞争趋向“白热化”
- 这种饮品甜了中国人几千年,但这4类人真不建议喝
- 河南省1949-2000年各市老牌白酒全揭秘,谁是你心中的“酒王”?
- 泸宜遵“酒悟天下”系列一:为什么泸、宜、遵产区盛产美酒?
- 王咀牌赐窖酒
- 酒瓶堆满屋,父子都喝醉,家在裂缝里喘气
- 从古道到新路,白沙液在老名酒振兴中探寻穿越周期新赛道
- 这个酒庄凭什么斩获“中国酒类流通 20 年创新企业奖”?
- 2025中国酒业上市公司品牌价值榜TOP30发布
- 石门米酒:深山藏佳酿 古法酿醇香
- 醉怀川丨怀川玉液:焦作地产山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作
- 自酿米酒,配方和比例告诉你,一看就会,保证一次做成功
- 徽酒“决战”次高端:口子窖掉队 迎驾贡酒夺位
- 鱼台文创:非遗文化体验
- “酒”这么玩|泸州江阳区30款佳酿亮相酒博会受青睐
- 重走贡酒路,剑南春的古道与新途
- 川派浓香入门之选,迎合80%消费者口感,却只卖出厂价的纯粮酒
- 浙江省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食品监督抽检结果(2023年第8期)
- 一老板为女儿举办婚宴花52万,怀疑采购商吃回扣拒付款!采购师傅:他要东星斑帝王蟹
- 浙江一老板为女儿办252桌婚宴共花52万元,拒付款,采购师傅:准备打官司
- 【圈人物】大漠酒香,续写楼兰传奇专访新疆楼兰酒庄董事长许志良
- 沁水往事小小说之三:门岗老孟
- 口子窖:白酒卖不好影响业绩增速,“有潜力”经销商赊账8个亿
- 楼兰酒庄:丝绸之路上最美的酒庄
- 四川省泸州市市场监管局关于4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3年第二期)
- 国宝窖池持续酿造450年,泸州老窖将打造封藏大典文化IP
- 【鲁风圣韵】 诗刊 第8期 山东诗词研学走进济宁采风作品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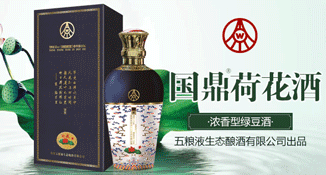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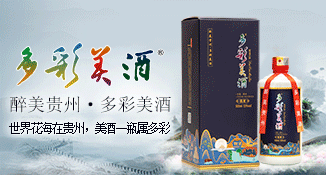


我要加盟(留言后专人第一时间快速对接)
已有 1826 企业通过我们找到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