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原(四百零二)|移民村

移民村
文/张鸿志
“哧-哧-哧”窝头炉子上的燎壶,沸水滚滚,雾气袅袅。邢大娘叼着烟卷儿快步走过去,提起燎壶浇在两个大茶缸子里,顿时冒出浓浓的茉莉花香味。邢大爷从屋里走出来,揉着惺忪的眼睛。老两口坐在板凳上,端着茶缸,摇动着头吹拂着漂在水上面的茶叶,慢慢地轻抿着。这是初夏的早上,还不到六点钟,这对“老济南”就“滋润”上酽茶了。在他们看来只有“喝透了”这才有精神才有活力,这也是济南人的习惯。这时,职工大院里开始骚动起来了,忙碌起来了。做饭的,挑水的,喊孩子起床的,晾晒孩子尿床被褥的,站在门口刷牙洗脸的,打扫卫生的,跑厕所的,鸡鸣狗吠此起彼伏……随着大院的锅碗瓢勺交响乐,开启了新的。
壹
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北镇运输公司(现交运集团的前身)职工大院的日常生活剪影。这个大院历经了近七十年的风雨沧桑,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变革与企业的升降枯荣,也充满了烟熏火燎的生活气息,承载着那些人情物事,它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记录着流年岁月的悲欢离合,蕴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大院的创业者和公司的同事们,走过了极其艰苦的创业之路,虽身在困顿窘迫中,仍积极乐观向上,友善助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为发展当地经济,方便人民群众的出行,为胜利油田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代表着滨州代创业者的精神风貌。
北镇汽车运输公司始建于1952年,第二年正式营业,也是老惠民地区最早的企业之一。1956年建成这个职工宿舍大院,一小排平房住七户人家,每户一间半,三小排形成一大排,前后五大排,东西各有一个公厕,南北各一口水井,周围拉起了高高的院墙,这就能够称其为大院了,这在当时也是北镇更大的院落之一了。省交通厅从济南运输公司整建制划拨的大部分车辆和人员,以济南和周围地区的人员为主。公私合营后又从青岛调来几十部车和二百余人,这些人大都来自胶东半岛,烟台威海人居多,也有一部分来自潍坊地区的。又陆续从徐州、德州等地充实过来不少人。还有从上海、浙江、南京等地分配和抽调的学生或专业人员,以后大部分人员又陆陆续续地回到原籍。有不少的驾驶员,曾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他们都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在这些外来组建公司人员中,以汽车驾驶员、汽车维修工为主体,管理及后勤保障人员为辅。但很少有当地老北镇人,至今也不得其解。
显然,这是一个大杂院,规范地说是移民院。这个大院住户没有复杂的宗亲关系及沾亲带故的裙带关系,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省交通运输厅计划部署下,公司得到了迅猛发展。地域面积日益扩大,下辖单位增多。截至70年代后期,素有“南到沂蒙山,北到渤海湾”之说。公司辖有11个汽车队,19个汽车站,29个代办点,1个修理厂,1所技工学校。职工2500余人,营运货车500余台。这在当时的惠民地区当属更大的企业之一了。不管人员增加了多少,地盘拓展了多大,基层单位组建了多少,公司核心层就住在这个大院里,它是大脑神经指挥中心。那时,还沿用了部队编制,运输连,修理营,公司即团部。还有与此类似的个人的称谓:称呼有工作、有文化的女性为“大姨”称呼没工作的家属女性为“大娘”“大婶”其个中缘由我曾用心研究过,至今也没有厘出个端由来。
贰
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没影响到大家乐观向上睦邻友好的精神状态。夏日的晚上,常常是住在一排的住户围坐在一起,如同一家人,摇着蒲扇聊着家长里短,海阔天空。孩子捉迷藏,你追我赶,疯狂游戏 。谁家偶尔包水饺改善生活,那一定逃不过邻居的眼睛和嗅觉。于是,邻居间互送水饺,或者送几张饼,已是习以为常。杨大娘家已生育四个子女,一下又生产了三胞胎,使原本就拮据的生活一时陷入了困顿。汽车一队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别出心裁,买了一只哺乳期的山羊作为救济品,这确实是更佳的救助办法。顺手抓把草喂羊就可以挤奶喂娃,而且奶质新鲜又可持续长久。那时,每户生育五六个孩子十分正常。虽经历了生活困难时期,但也都健康地活下来了。在大院西北角,邻村一贾姓人家“开疆拓土”拉起院落建起了房子,更雷人的是这位“英雄妈妈”一口气生了十个娃。到了晚上睡觉时,要端着煤油灯,摸着脑袋瓜一个个查看孩子来全了没有?是否还有落在外面的?多年以后,这家的男孩高大魁梧,女孩亭亭玉立,个个都精明强干,也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生活条件的简陋,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烦恼与不便。做饭时,只有使用放在天井的窝头炉子,烟熏火燎,炊烟袅袅。吃水要提着水桶到井口排队,还得通过旋转辘轳上绳索,将水桶从井中提升到地面。早上去公厕更是尴尬,排号是必需的,关键是“坑”不应求。外面的人捂着肚子弯着腰来回打转,嘴里还“哼哼唧唧”的,“行了吧?我快不行了!”而厕所里蹲坑的老哥还从容地读着《参考消息》呢……
越是生活艰苦,人们就愈加团结友爱。我的邻居小勇子是家里五个子女中的男孩。有一年初夏,五六岁的小勇子伙同几个小朋友去东边农村摘果子,被人驱散,慌不择路,竟然把自己弄丢了。父母着急万分,大院的前邻后舍闻讯后,自发地组织了四五十人的寻娃大军,手持手电筒,浩浩荡荡沿路寻找。喊叫声此起彼落,手电筒的光束纵横交错,如同夏夜的闪电。喊叫与光束打破了夜幕里的宁静。在一个草垛中,终于找到了熟睡的小勇子,把孩子带回家已近子夜时分。丢失孩子这么大的事,家长不是选择报警,而是依靠大家自发营救,说明了大院里人们深厚的友爱和高度的信任,彰显了团结就是力量,充分体现了一家有难,大家支援的互助精神。
叁
这个大院从来就不缺酒,似乎酒是消除疲劳,安神定魂的一副良药。这也与本行业劳动强度大、精神压力大有关。同时,也是加强交流,增进感情的一种渠道。驾驶员出差回家,必定吆喝三五酒友,聚在家中酣畅饮酒,发泄一番心中的块垒,说笑怒骂皆在酒中。 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驾车出行了。尤其到了过年时,从大年初一晚上,轮流席开始了,今天张家,明天王家,后天李家……不出正月就是过年。劳累一年的驾驶员维修工,也彻底放下顾虑,尽情点燃自己。就像浇花浇草一样,一定得浇透了,来年才长得更加茁壮。自然是高调划拳,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一开始还和风细雨,“弟兄俩好,过年好,再好好!”随着酒精发挥作用,那酒场就像战场,“四喜来财啊!五魁首啊!六六大顺啊!”只见“博弈”双方酒酣耳热,四目圆睁,气喘吁吁,脸红脖子粗,吼声如雷,声浪一浪盖过一浪,划拳声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情绪激动者,甚至是脱掉外衣,露出蟹螯般的腱子肉,展现着男人的力量。此期间,满大院飘着酒香,猜拳行令声此起彼落。七八岁的男孩子们跑到谁家都一样,贪吃口肉菜,家长们再“强灌”口酒,就撒丫子跑掉了,换个人家还是如此,一晚换几个人家也都是这样。直至酒上头了,孩子们头晕目眩,如土委地,才算过完了这个晚上。那时常喝的酒有山东白干、景芝白干、乌河大曲、兰陵大曲、兰陵特曲等,这些酒牌标记着那个年代,印证着那段历史,蕴含着那些故事。俗话说得好:“船家孩子会凫水。”大院的第二代就是闻着酒味长大的,及至参加工作了,充分发挥出了“”法宝,在酒局上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
毋庸讳言,自古就有“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一说。但这里指的是封建时代的一些肮脏产物。都是从事涉黑、绑架、人贩子、敲诈勒索、损人害人的勾当的犯罪分子。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劣迹污垢早已被扫除干净,和我们不沾边,完全两码事。汽车驾驶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驾驶员是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物以稀为贵,那时,张北公路(张店——北镇)上基本上是北镇公司的车,社会车辆寥寥无几。后来,胜利油田的进口车才逐渐增多。尤其计划经济时期,民间流传着顺口溜 “一是权,二是钱,三是方向盘……”民间俚语切不可完全当真,但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方向盘”地位之高。
肆
因为地域不同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人们之间的交流来往也有选择性和倾向性。这也是移民院的一个特色。以青岛人为代表的齐文化,喜欢吃海鲜蛤蜊喝啤酒,显得浪漫洋气;而以济南人为代表的鲁文化,喜欢吃九转大肠喝高度白酒,看起来豪爽实在。南北方差异也是如此,南京的刘大爷喜欢吃鸡肠鸭肠,就在家门口翻来覆去洗涮,天津的刘姨掩鼻而去,皱着眉头,顺便丢了句:“这是嘛玩意儿啊?”徐州的苏伯伯闻不惯无棣人吃的虾酱,而无棣人老王也吃不习惯徐州甜兮兮的蜜制蛋糕,安徽符离集的宋伯伯就说符离集的烧鸡远比德州的扒鸡好吃,德州的薛大爷反唇相讥,两人“约战”是日,俩人手里各自掐着一只各自家乡的烧鸡、扒鸡,自夸自吃,交换对比,吃得是津津有味。结果却让裁判吃了个肚儿圆,最终也没能分出个胜负来……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不同的生活圈子,但并没影响大院的整体团结和睦。
在最后一排两间平房里,分别住着两位老人。他们的身世非同寻常,是参加次世界大战的华工。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提出了“以工代兵”策略,在华北地区招募14万华工,山东人占了多数。这些华工赴英法者居多,到欧洲战场是以挖战壕、修路架桥、汽车运输及维修为主。这四个人是批援法的,经过简单培训,驾驶汽车运输战场物资和后勤保障物资。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故乡山东,几经辗转,在公司成立初期就来到了北镇运输公司,还是担任驾驶员,他们可能是公司驾驶资历最老的驾驶员吧。我们有记忆时,他们就已是垂暮老人了,长期住在那两间平房里,和外人没来往,也不知有无家室,以后就不知其所踪了。
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四川的黄大爷,他参加过中国远东军,入缅对日作战。10万大军,阵亡6万,战争极为惨烈。他负重伤被送回国内养伤,后又参加革命工作,组建公司时来到北镇。他高高的个子,少言寡语,看起来有些忧郁。老伴黄大娘却相反,乐观敞亮,快言快语。自从父母搬离大院我几乎没再回去看看。几年前,我去大院悼念一位去世的老人,黄大娘大声喊我乳名。这些年喊我乳名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在大院里听到喊叫“五子”声十分亲切,竟然找到了那份久违的乡情还有幽幽的乡愁。那年,黄大娘已八十八岁了。儿子十分孝敬,在西区给她买了新房子,她说不习惯,仍旧执拗地住在老宅子里。“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大院的代老人、代创业者,日益枯萎凋零,渐渐终老逝去,不免令人唏嘘不已。
伍
大院里粗犷的驾驶员有着高度的觉悟和服从意识,有着超乎寻常的吃苦耐劳的精神。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战略位置,将全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省市区。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是指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包括交通运输、邮政通信、主要燃料和农业、轻工业等战略后方基地建设。公司派出一个车队的驾驶员,分拨50辆解放牌汽车,与来自兄弟公司的同事,为修建成昆铁路运送石材等各种物资。在深山老林中运输物资,切身感悟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克服了水土不服、蚊虫叮咬、野兽侵袭,曝霜露,斩荆棘,圆满完成了重点项目的建设。而去支援三线建设的驾驶员,来自大院的不少,而且是车队的灵魂。那些当年支援三线建设者,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但一提到三线,眼睛发亮,情绪激动,止不住地侃侃而谈。高师傅说:“我们穿梭在险峻的大山里,既流汗又流血,行驶在悬崖峭壁边的碎石路上,像是在刀刃上跳舞,时刻高度紧张,绷紧着安全驾驶那根弦。兄弟公司就出现了重大事故,有的连车带人坠崖的,也有扎入大渡河的,永远地留在那里了!”说到这里,高师傅陷入了沉思,神色凝重。郭师傅为缓解气氛说起了轻松幽默的话题:“我们有时也捎带着帮助偏远的农村里运点农产品。有一次,两个姑娘为了答谢我们,精心准备了两筐草料,要喂喂汽车这头‘牲口’。”巴山蜀水,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留下了他们的汗水,留下了他们的青春,甚至留下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70年代初,夏天的晚上,大院的人们刚坐下来准备吃饭,公司高音喇叭广播,要求大家立即去北纺(原滨州一棉)灭火。他们撂下手中的筷子,撒腿跑向大门口,几辆货车已停靠等待,人们纷纷翻上车,迅速赶往失火地点。消防车已赶到开始施救,职工们端着一盆盆水泼向火舌,同北纺的职工一道,冒着被大火吞噬的危险,搬离棉纱布匹,打出一条二十几米宽的隔离带。经过几个小时拼搏,终于扑灭了大火。等回到家,个个像落汤鸡,满脸的污垢,如乞丐一般。由于极度的紧张和劳累,他们吃不下一口饭。在他们眼里,财产都是的,没有单位之分,更没有你我之别。现在,有的人经常说“就像邻居家着火了一样”其实那是他家自己的事。但不管时代怎样更迭,也不管世道如何变迁,当灾难临头时,那个勇于挺身而出的人,一定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一定是泰山般的汉子!这就是大院的那帮男爷们的气概与大义。
胜利油田的建设开发,对于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艰苦奋斗、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建设初期,油田自备车辆很少,绝大部分物资由我们公司运输。尤其组织货车自淄博辛店拉石头运至东营孤岛填海,建立拦海大坝,公司驾驶员发扬了精卫填海的精神,为油田采油量大幅度提升作出了突出贡献。大院的驾驶员每每说到这一章时,也是满满的自豪。他们吃在车上,住在“解放宾馆”(解放牌汽车)和“东风旅社”(东风牌汽车),风餐露宿,翻山越岭,行驶在海滩泥泞之地,再次彰显了艰苦创业精神。1987年初冬,二十多辆运送石头的货车被海水吞没,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幸亏油田组织人员抢救及时,没造成驾驶员伤亡。那一片汪洋都不见的浑浊海水,却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陆
70年代初,公司开始改善职工大院住宅条件,花费十年工夫,拆除平房,建起二层小楼,相当于现在人们常说的“联排别墅”朝着“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70年代能住上这样的楼房,在老北镇确是一大景观,在惠民地区也是首屈一指的,外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住上带着小院的二层楼房,职工体面自豪,荣光无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几米长的院墙犹如薄薄的横膈膜,似乎阻断了那畅通无阻的烟火气,降低了人们交流的频次,隐隐闻到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
改革开放后,提出“发展经济,交通先行”的要求,也给道路运输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公司着手实施奖励措施,大大激发了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效益节节攀高。1978年被交通部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年上缴利润960万元,在惠民地区是名列前茅的明星企业。那时,黄河北岸没有一寸铁路,私家车为零,社会车辆屈指可数,更遑论航空大宗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和百姓出行绝大多数由运输公司来完成。公司的荣誉花环由驾驶员及维修人员的汗水和鲜血浸润盛开的。岳振堂伯伯系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先后驾驶过客货车,安全行驶120万公里,相当绕地球30圈,在全省名列前茅。驾驶能手赵伟政获得全省汽车节油大赛名。省劳模李代刚、齐书文、赵德松在驾驶岗位上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翟所英、田辉在车辆维护与保障方面默默无闻地做出了贡献。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因公殉职的驾驶员王玉桥等同志。正是这些大院里的劳模和公司的先模人物的无私奉献甚至献出生命,推动了公司这艘大船乘风破浪,驶向理想的彼岸。大院里走出去的三位党委书记也先后履任地区交通局局长、无棣县委书记、地区外经贸委主任。
令人欣慰的是公司现任领导班子,通过“止血、疗伤、强身健体”进一步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实施再次创业,朝着建设“六个交运”的目标砥砺前行。
柒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个老院已近古稀之年,大院的第二代业已退休或即将退休,他们中有救死扶伤的医生,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记者,有三尺讲台奉献一生的教师,有勤勉为民的政府官员,有铁面无私的检察官,有成功的企业家,还有艺术家……但更多的是继承前辈的衣钵,从事道路运输与维修业的。这些人群中,有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了公司的领导岗位,有的成了技术权威,甚至成为滨州市的专家委员会成员。祥伟兄是大院二代的代表,在人民医院担任科主任、主任医师,可谓仁心妙手。我们坐在一起经常聊起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些陈年往事,他曾颇有见地地说:“咱们这个职工大院存续绵延了几十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就是一个带院的村,就是一个移民村。”他总结得十分恰当精准——移民村。他的话题离总也不开有关移民村的内容。“自我参加工作以来,咱村里来找我看病的咨询的拿药的,多了去了,三天两头地来。头些年,程大娘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她推着瘫痪的程大爷来看病,我得从头到尾全程服务,一忙活就是将近半天。唉!这几年呐,咱村里的长辈日益稀疏,找我看病的越来越少了。”此时正值盛夏,我却感觉悲秋渐近,心里掀起一阵涟漪。他接着说:“咱村里一个发小,自小患大脑炎后遗症来找我,我更得跑前忙后,看完病我帮他打上车。真怕他丢了!谁让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来。”我也深有感触,几十年过去了,村里的人干啥的都有,像王氏兄弟二人那么的还是极少数。哥俩学业,在不同领域颇有建树,尤其二弟在能源行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和奖励,在业内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兼任多个单位的独立董事,给移民村争得了荣誉。
几天前,我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移民村。父母自2007年因病搬至滨医附院,我就再没进过这个家门。期间,房院几易承租人,现在是一家算卦看风水的承租人。家里的结构完全变了,色彩也完全变了,没有家的丝毫痕迹,闻不到家的丁点儿味道,我甚至怀疑这是我曾经生活过四十多年的家吗?那两棵43岁的香椿树原本在院内,因渤海五路拓宽院子收窄,就把它们排挤在外,像无助的弃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树枝杂乱,枯枝折断。此时,成群结队的暮鸦掠过枝头,“哇---哇”的鸣叫让我感到一阵凄凉。望着前面那栋楼,墙皮剥落,红砖凹凸,窗锈斑斑,便不由得仰天长叹:繁华落尽,故人离去!这个村早已过了三十年的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一甲子,以后去向何处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移民村竟然变成了小区,楼房错落有致,气势恢宏,处处彰显着不凡的品位与格调,尽显大气高端雍容华贵之风范。小区门口摆放两只铜制狮子,中间显眼处,用不锈钢铸成的巨型方向盘,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有梦想,就有希望!
下一篇:“兴安岭酒业”生产忙 酒香飘四方
推荐资讯
- 婚宴用酒怎么选择呢?2020-09-01
- 瓶装酒存放必须要知道的细节 !2020-09-01
- 散酒中存在哪些重要指数?2020-09-01
招商推荐

- 原浆进口OEM贴牌葡萄酒
- 类型:
- 热度:

- 我要加盟
- 白酒动态
- 啤酒动态
- 红酒动态
- “十四五”将收官,这些“中国制造”点亮生活
- 内蒙古市场监管局抽检酒类样品19批次 合格18批次
- 已经消失的7种安徽白酒,最后一种你都没听过…
- 浙江省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示(2024年第5期)
- 日本清酒起源于中国黄酒,为啥卖那么贵还销那么好?原因值得深思
- 白酒行业变天了!小瓶酒圈粉年轻人|白酒行业猎头公司
- 「酱迷解惑」精酿小郎酒与小郎酒,价格相差不大,口感有何差别?
- 每一年纪念郎酒品质好坏有点随机,今天对比品鉴
- 山西省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5年第十二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告
- 安徽人请客不怎么用茅台,而是偏爱5款“良心酒”,行家直言会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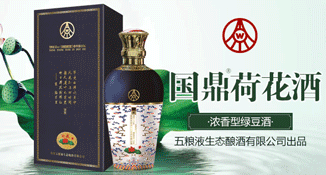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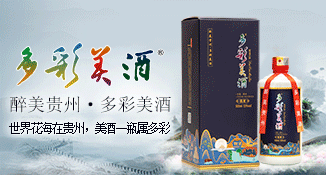


我要加盟(留言后专人第一时间快速对接)
已有 1826 企业通过我们找到了合作